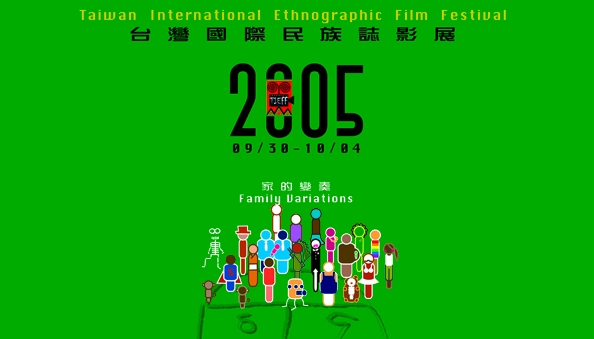清晨與夜晚/振作與頹廢的對話
王宣一、陳俊志
(本文刊登於9/28之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 Hi,俊志,你在線上嗎?
我在洛杉磯,剛從Temecula Valley回來,那裡是一個小的wine country,這天氣,秋高氣爽的,喝幾口小酒真適合聊天。
◆ 宣一,我從台中搭夜車回來台北了。一路上記掛著要在網路上找到飛到美國的妳,又聽說有個颱風要來,夜車上總是睡不安穩。
☆我以為在美國西岸和在台北習慣熬夜的你,時間上可以配得剛剛好,網路零時差,沒想到一上線便是忘了白天黑夜,我得在友人的電腦上按上MSN、 skype和中文輸入法,一件件弄好,你卻已到台中跑場子,我只好先去散步一回,再給自己倒個小酒。
我想起那天《無偶之家,往事之城》台北電影節首映,下著不小的雨,站在台北社教館的外面找不到入口,想找個人詢問,不知是不是因為捧著一束花讓我有點害羞,很奇怪的,不過是問一個入口處,那天竟會讓我那麼害羞得有點開不了口,我是個還算開朗的人,那時刻內心裡那個內向的我竟突然跑了出來。呆站在那裡好一會兒,才看到一個穿著背心的男孩匆匆經過,突然覺得這個人調子對了,便大喊「請問電影在哪放映?」沒想到男孩竟也回我,「我也不知道耶。」然後更匆忙的跑了。
幸好這回開朗的那個我又回來了,捧著花緊緊追著那人的腳步,但一攸忽的,那人就不見了,不過還好很快就找到了入口,人聲沸沸,光影斑斑,和外面的冷雨完全不一樣,不過立刻的,我又發現,首映之前沸騰著的喧嘩之中,和我同族的異性女子實在不多,找著一個問她,「請問導演在哪?」她指指一群人中的一位說就是那個,我轉頭又看見背心男孩也在其中,心想不會是你吧?這人也搞不清入口處,不會就是導演吧?但當我疑惑的再度確認,沒辦法,真的就是了。
但是你還是動作敏捷的在人群中穿梭,眼裡似乎完全沒有我這種落單的異幫女子的影子,或是因為我抱著那束花,你也猜到可能是我,害羞的假裝沒看見,我只好追著你轉,叫了好幾聲「導演」,終於等到你回過頭來。我們第一次相認,相互笑著說,「剛才問路的時候不知道就是你呢。」然後你張開手臂,簡單的給了我藝文圈裡表示友善但有距離的擁抱。
老實說,坐在整場同志,尤其是男同志當中看電影,真是一個奇怪的經驗,雖然總想有機會到同志電影院去體驗一下,但總怕被人嫌。這回我的左右空位果然沒有男同志願意坐下,一開始心裡其實是有點不是滋味的。
但是那天,和整場的gay坐在一起看一部談同志的紀錄片,原本是孤獨的我,竟然內心充滿了熱情。熾熱的內心和一部冷調的紀錄片。
◆ 拍紀錄片十年了,我總是過著飄浪的生活。拿著攝影機看著的現場,往往蘊藏著我用盡所有拍攝,剪接技術,說也說不出的險惡的秘密。拍片是冒險,是尋找,是闇黑中找光亮,終究帶來巨大的抽象的快樂。
在台灣拍紀錄片是沒有錢的,得學會過物質上谷底的樸素生活。我找到一種流浪藝人的過活方式,一場一場放片跑江湖,在大霧驟雨中迷離辨路,總是可以撐著生活,從來不曾放下攝影機。DV長在手上,變成身體四肢,竄升亂蹦到腦裡長出奇異的花朵。
妳提到《無偶之家》首映會紛亂的場景,在小說家的敘述下有趣繽紛極了。但我的心揪緊在他方,沒能有妳的眼睛看到這些。影片中逝者的朋友們,那一夜紛紛來到放映現場,在他死去的五年後,第一次就要知道錯綜複雜隱藏的愛滋秘密。好多男同志朋友看到葬禮那幕,簡單的畫面夏日蟬聲隆隆,他們掩面流淚逃出戲院沒法繼續看完也曾發生在自己身上那麼相似的最痛的時光。
於是,阿嬤和蔣姨古典優美地唱著台語悲歌,「彈吉他唸歌詩,已經過五年。做得一個流浪兒,也是不得已。」作為一種溫柔世故,老人迷離眼光看著倏忽而過,同志人生的理解。
妳也在的首映現場,於我彷彿一場心思複雜的遲來的葬禮,倖存的人們看著逝者在流動的光影中重活一次,燦爛奪目降臨我們的宴會。
「雪花片片飄上那些歪歪斜斜的十字架及墓石,飄上小小園門的尖茅上,飄在那些荒涼的荊棘上。」喬哀思小說集《都柏林人》卷尾的字句,飄浮疊影在過去台北滿街廉價VHS租售店裡,隨手都可租到如今再也難尋的約翰‧休斯頓的最後一部電影,《逝者》。
☆ 讀小說,最怕議題最怕熱鬧,看電影,受不了煽情,看記錄片,最忌嗜血。
非常非常意外的是,講同志的電影,可以如此雲淡風清。紀錄片要的是沈靜,不是自溺,有議題的題材,要拍到內心,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拍同志生活、拍同志之中愛滋病者的生活,很擔心看到的是過於自戀於自我構築的世界,不論愛情,只講做愛,自陷於同性戀者的共犯結構而不自知。
意外的是,抱著那樣的心情到現場,隨著片子進入,電影卻平實得令人嘖嘖稱奇,我以為有些情節走到那裡,會開始暴烈了,可是竟那樣幾個鏡頭輕輕帶過,你是為什麼可以這樣簡單的拍同志議題愛滋議題這樣明確的紀錄片的?我知道一些出櫃的同志,我以為拍過同志電影《美麗少年》的你,也許是長期生活在異性戀霸權的社會機制裡,因此出櫃之後,就擔心別人不知道他們是同志,生活方式、做愛方式和異性戀不一樣。所以有任何機會,在小說裡在電影裡,在各種藝術形式的表現之中,不錯過詳細描述同性之愛的細節,那些無關乎同性異性之間慘不忍睹的粗魯或唯美,那種陰莖與陰莖或陰蒂與陰蒂式的對話,只會讓異族們(異性戀)更加排斥閱讀同性戀的真實,辨識不出同志的原始面貌。包括在網路上的帳號都不放棄要告訴人家你是gay的死忠gay,是那種碰到機會就寧可錯殺不可錯過的激進份子。
我想你是成長了,拍了那幾回片子,知道什麼是收斂,什麼是隱藏,真的很怕看到那種所謂的忠實呈現,卻不知節制的赤裸,毫不遮掩的性愛(無關乎同性異性)。你知道,我寫小說,也最不喜歡議題,瑣碎、生活、平淡的風格是我希望的最高境界。我很高興看到這部片子,同志和愛滋不過是一種內容,並不是議題,我覺得做為一個gay,你是成熟了,成熟到不再以gay為唯一的發聲,雖然你拍的片子仍是gay,但我相信只是因為你的生活圈是那樣,你是拍一種生活,你看到接觸到的一種生活,你可以認識並某種程度了解的一種生活。對吧?其實你只是比較有機會接觸,因為你和那些所謂的老gay的老台客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樣的。
◆ 我好高興我衷心崇拜的小說家朋友們,都看出這部片子的好處──我終於把紀錄片拍成像小說。小說家創造人物,編排情節,統攝意義,無一不是殫精竭智的神秘附身過程。但是紀錄片每分每秒都是真實生活,如何達到虛構小說難以言說的平淡中見複雜,大概就是這次我給自己的功課。而這次功課真是費盡氣力,瀕臨死亡邊緣學來的。
☆拍紀錄片其實有個問題,導演本身到底要介入還是抽離片子本體?對不起,我想這樣粗淺的問題,是最難回答的。基本上,我覺得即便是紀錄片,也是一種創作,你無論如何是不可能複製別人的生活甚或自己的生活的,什麼事情透過鏡頭,就屬於導演的了,不再是片中人物的了,是被影像化被扁平化立體化被解讀過被包裝過的東西,不論導演如何忠實,不論角色如何不自覺被記錄,那種真實是有角度問題的,有導演的種種偏執與不解的死角的,有技術上無法克服的問題的,所以即便是紀錄片,也是一部電影,只是演員可能沒有劇本而已。
沒有劇本的片子,有時比電影更戲劇,有時比真實人生更平淡,但觀眾就只是觀眾,不必是特定的族群,所以我想記錄片要呈現的,會是堆疊的是重覆的,是那種不一定要在散場之後立刻可以有議論的,應該是要沈入心靈深處,偶爾在某些時刻,跳出來撥動你的心弦一下的。
我相信你在讀小說或看電影或聽一場音樂會或看一場藝術表演之後有過這樣的經驗?我對這樣的經驗是常常碰到的,但是我很少在當場,激動的站起來拍手,流淚或想熱情的追星,我會喊安可,常常是為了撈本,但卻在很多平凡的時刻,突然的,一種畫面,一句小說甚或連續劇裡可笑的對白適時的跳出來,攪動平靜的心靈。
因此那天電影放映之後的座談會,我就有點受不了同志們的發言,一些同志還是激動的掉入同志們的共犯結構而不自知。現場那樣的反應,我覺得有點可惜,很多同志都忘了還有很多不是同志的族群似的。全場gay和少數的異族,實在有點可惜。但是這樣的題目,我想更應該的是要給異幫看才有意義吧,不論你的目的是要控訴或者只是要呈現同志生活同志愛情,目的應是抵抗異性戀的霸權主義,希望社會給同志一個位置,給同志和社會一個自然和協的空間,但是首映會吸引的卻大多是同志們,甚至是男同志們,那不應該只是在小圈圈裡存在的片子。既然希望讓異世界的人們接納他們了解他們,電影應該要想辦法吸引他們才是啊。
◆ 妳提到介入與抽離,收斂或呈現,在這些創作的大哉問中,我是個人格分裂的紀錄片人。拍《美麗少年》時,我依本能而行,先鋒世代的小gay們亂竄的動能在攝影機前後沒有規則地流動。騷動的力量太強讓我沒有空間思考故事的規則或結構。大火快炒,反而幸運地留下男孩們原汁原味動盪的青春。
☆ 愛情,無關乎同性或異性,所以我很喜歡這片子的原因是,這是一部有關乎兩對情侶的故事,主角是同志,是同志愛情,最後因為愛滋病面臨生離死別,愛滋就像癌症一樣,是一種病,但並不悲情。雖然很多時侯,我們因為愛滋、因為同志霸權而無法避免。
我參與一個痲瘋病患的救援組織,曾到四川涼山州和一群痲瘋村的孩子們玩耍,看過他們被禁錮在小小的山村裡的生活,但他們自己並不悲情,大部份都很認命,認命並不是沮喪,他們很努力的爭取一種生活,一種平凡人的生活,受教育的機會、工作的機會、下山的機會、取得身分證明的機會,僅只這樣,他們不會因為這樣的生活而哭,他們不會因為被拒絕而哭,不會因為被嘲笑而哭,是我們看到那樣的生活才忍不住哭了,悲情的是我們,灑狗血的是我們,他們有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感情他們的愛情,只要是情是愛,就是一種令人動容的關係,一種平凡的動容,一點都不特別偉大或可恥,但他就是在不知不覺中攪動你的內心深處的某一種情愫,很細微很慢,但是可以很深。你是喜歡這樣的感覺的吧?一種不必言明是同志電影,是愛滋愛情的關係的感情吧?
◆ 《美麗少年》上片的成功,當年在同志運動最狂飆的年代是個活潑的出口,我身不由己遠離創作,置身熾熱的第一線。只是,議題的燃燒消耗著拋頭露面的表演者。沒有時間沒有餘裕靠近自己真正的安靜哀傷。我一有機會繼續拍片,《幸福備忘錄》竟變得內斂沈潛,冷靜到燃點最低的臨界。女同志湯姆漢娜感情生變的暴風雨催折中,我依然嚴守古典劇場訓練,結構森然有序的二幕劇,保持一定的視點與距離。遠離所有技巧。
一直到《無偶之家,往事之城》,我才有機會傾聽心底沈默喧嘩的文學呼喚。經過漫長的蹲點等待,謹慎運用我累積複雜的電影技術,像一個深知自己美貌的嬌羞少女,我迫不及待走上舞台,迎接評論者鑑賞的目光。
拍《無偶之家》長達五年,細節太多繁瑣的記憶讓我恍惚忡悚,我特別記得一個有狗和微雨的冬天夜晚。那是困在這個拍片計畫的第四年,不但錢早已用光,我開始出現憂鬱症前兆,足不出戶奄奄一息。前任男友把小狗關在陽台狹小空間整日低嚎,沒人照顧牠。我的狀況比狗還慘,困在無路可出的創作苦繭中,常常有自殺的念頭。我拍攝的人物眾多,時序混雜,彼此互不交涉,敘事形式前衛與寫實並置,衝擊辯證影片深層的意識型態。初剪版本根本沒有人看得懂。
物質的苦沒什麼,精神的苦卻讓我想死。我自己完全找不到方法走出影片的困境。
☆ 創作並不曾讓我想死,反而讓我怕死。我好怕寫了一半就死了,別人看到我未曾寫完的東西,所以寫小說的時侯,我努力過正常的生活,我每天跑步五六公里,早起早睡,以便振作起來從事頹廢的創作。 所有那些外在的喧鬧,都必需在寫作之前體驗和完成,否則我只能做片段的記錄而已,創作是要結構的,在工作時,我只需要寧靜和規律,我不需要酒精和朋友。所以有時候遇到瓶頸,我就一個人去旅行,在開放又密閉的世界裡,尋找一種孤獨。
創作過程當然是一種孤獨且頹廢的行為,所有書中人物都附身在創作者身上,寫作者同時扮演多重角色,人格必然分裂,精神必然恍惚,如果沒有儲備些精力,是無法應付那樣耗力的過程的。尤其在最後的關鍵時刻,封閉一切外在,完全進入情境之中。我很享受那樣的經驗,就和嗑藥一樣,有時侯情緒超high,有時侯迷離淒涼。但還好終點我可以走出來,然後我就放下了,用剩餘的力量繼續我時髦頹廢的玩樂。
◆ 那時,愛我的朋友們怕我死掉,帶了紅酒來到我一向好客的公寓。卻看到奄奄一息孤獨的我和狗,以及用力過深晦澀難解的故事的碎片。旁觀者清,聰明的他們用自己的方式試著幫我理出故事的頭緒。那是艱難的意志拔河,我如何肯放棄自己繭居苦思的藝術靈感與他們尋常平凡的故事協商?!我記得那個冬夜好長,好多話語在紅酒與我的執念中來回穿梭,我深知朋友愛我不會害我,不情不願一點一點用筆記下,仍然頑強執拗地與他們辯論。 門外的狗嗚咽叫著,讓我們心痛。
然後我們聽到冬雨落在安靜的屋頂,世界在夜色中溫柔迷離。大家端了紅酒走上屋頂終於徹底放鬆。一向冷靜如雪的美女小說家竟抱來被鎖住的小狗藏在她黑呢大衣的溫暖懷中。狗兒畢竟年紀還小玩心好重一次一次上下撲竄,在這落雨的屋頂和她長曳的大衣翻滾在黑夜淡成遙遠的剪影。我好像明白了狗是一種象徵。My life as a dog,我一定要結束這困居的狗臉的歲月,找到出路。
我開始大量看DVD,日以繼夜,用功做筆記,作夢都是結構與形式語言如何達到最合宜的神秘對話。我狠心捨棄原先龐雜晦澀的人物情節,專心經營一個簡單的故事,深思熟慮用我熟悉或想像出的技術在每一個環節,場景用心鋪陳敷衍。告訴自己別貪心,簡單中蘊藏複雜,然後自己才可以朝更複雜走去。
一直到現在,我的電腦剪接台上還留著那時手寫密密麻麻的筆記本,約略留下這次跨越真實與虛構漫長創作旅程中的點點滴滴。筆記中的吉光片羽指涉著不同觀念想法交涉糾葛的創作淵源。所以,宣一,對於真實與虛構,靈感與節制,小說家的技藝鍛鍊,妳一定也有自己的故事版本吧?
☆ 其實創作最難的部份我認為就是割捨,筆記本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片段,多是屬於冰山下的部份,能浮在水面上的,只是一小部份。往往我們看到一部爛片,就是有個不知取捨的導演。俊志,你從那麼激烈的同志運動中走過,你這回是必然要洗去很多東西的。五年一定累積了很多,可是最後要剪出那麼純粹的影片,是很不容易的,也許也因為是五年,你才能沈澱得更深,剪出清澈透明的精緻的作品。我一向認為創作是一種精緻行為,就是要含蓄婉約,那是一種內在的東西,怎麼可以粗魯,大魚大肉不知處理,一股腦兒全放進去,那只能做高湯,是基本工。
即使是拍紀錄片,真實還是經過了導演的內化過程,才能透過不同的鏡頭呈現出來,就算是新聞,我們也可以看到不同的鏡頭和不同的角度有著不一樣的解析(雖然台灣的大部份媒體永遠是扁平化了的統一觀點,人云亦云)。在創作之中寫下的故事,泰半是真實的,但真實並非對號入座,我寫《天色猶昏 島國之雨》不是沒有所本,但情節與角色當然是虛構的,你怎能說這就是某某某,老革命家的故事老革命家的愛情,數年之後,真實世界上演了更多不是嗎?
創作是絕對孤寂與神祕的,是極為複雜的內心活動,沒有人可以幫忙。即便是電影那樣的集體工業,導演也是必需有獨立思索的內在的,但是當作品完成,卻是一次澈底的精神治療過程。我可以想像你拍這片子的那五年的痛苦過程,那種煎熬,那種頹廢和沮喪,尤其電影創作和小說不一樣,媒介本身就那樣複雜,要很多部份的配合,尤其是金錢,小說家只要解決自己的肚子問題,簡單得多,但不表示情緒起伏就不大,但往往在創作過程就內化掉了。所以電影拍完,會有首映會有party,工作人員某種程度的要喝得爛醉,解放自己,但是這是幸運能完成的時候,如果完成不了,那社會上又多幾個躁鬱症了。我有一個小說家朋友很愛說故事,常常講很多好聽的故事給我們聽,每回說一個故事,擔任編輯工作的朋友就說,等你的稿子喲,但最後都沒有等到他的稿子,我們笑他,所有的故事都在他講述的過程完成了,所以他不必再寫下來,那已經失去創作的原動力了。
聽你說你的電影是要向你喜愛的作家致敬的時侯,我真的不能相信那是對我呢。我的書,從不曾暢銷,也未在文化圈裡有半點影響力,怎麼會有讀者喜歡呢?尤其你說你這部紀錄片的片名《無偶之家 往事之城》是追隨我的一部小說《天色猶昏 島國之雨》的書名而來,我更是嚇了一跳。可是片子看完,真的看到那頁致敬的字幕,我並沒有激動落淚,只有深深的不解。那本小說,我根本沒寫到和同志有關的章節,我以為一向在少數族群的同志圈中,似乎你們只願注目和自己議題有關的文化或事件才會被提出,而周圍的一些活躍在同志運動的朋友,很多時候眼裡沒有異性戀的旁若無人幾乎要惹惱我,因此不明白你這樣一個gay怎麼會對一本和同性戀無關的小說有興趣?
電影首映的開場上,我終於上台把花送給了你,你才說起你為什麼會成為我的讀者,我的粉絲。追究起來,和少年時的你讀到我多年前寫的一本和青少年成長啟蒙的小說《少年之城》有關,那本書是那個同志多半還隱匿在暗處時代少數的描寫到有關同性戀情感的小說,但是總共幾年賣不完四千本,我對出版社汗顏得不知所措,但沒想到對當時正是性啟蒙時期的你,產生了一絲光亮還是什麼?
◆ 這部片子某種程度是向妳與所有的小說家們致敬的。靈感當然來自妳的《天色猶昏,島國之雨》。影片中怡謀和阿生即將進入中年滄桑前回憶愛情之海,包裹在蔣姨與阿嬤歷經同志人生苦澀的世故豁達,一切輪轉宛如走馬燈。想像虛構的原型源自妳小說中飄浪失志的老革命家,當他被全世界遺棄遺忘孤獨病死,革命熾熱的異議無人記得,他卻在敘述者女子溫柔的愛情回憶中,永遠永遠有著「島國特有的細雨,無聲的灑在他的骨灰罈上,綿綿密密的將他緊緊裹住。」這是妳小說中的最後一行字。
同志作為性身份與人生的異議者流浪兒,也是不得已。那年讀到妳「少年之城」揭露主角哥哥死亡的同志愛情謎底,開始隱約嚐到愛情苦澀的我其實還不算真正痛過懂得。後來反反覆覆幾段戀情最痛苦時曾在深夜爛醉嚎哭,顫抖著撥手機一次次留言給決絕關機的戀人,在西門町老牌台客三溫暖大叫我想回家,知道自己的身體比死去的心還冷。同志姊妹淘怡謀在最深的黑夜趕來陪我直到我酒醒穩定,在清晨溫暖的早餐攤上喫著熱燙的味增湯與壽司,我細細回想著這個劇烈變化的三溫暖之夜。當時我並不知道,自己會變成說故事的人,多年之後拍下怡謀與台客三溫暖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