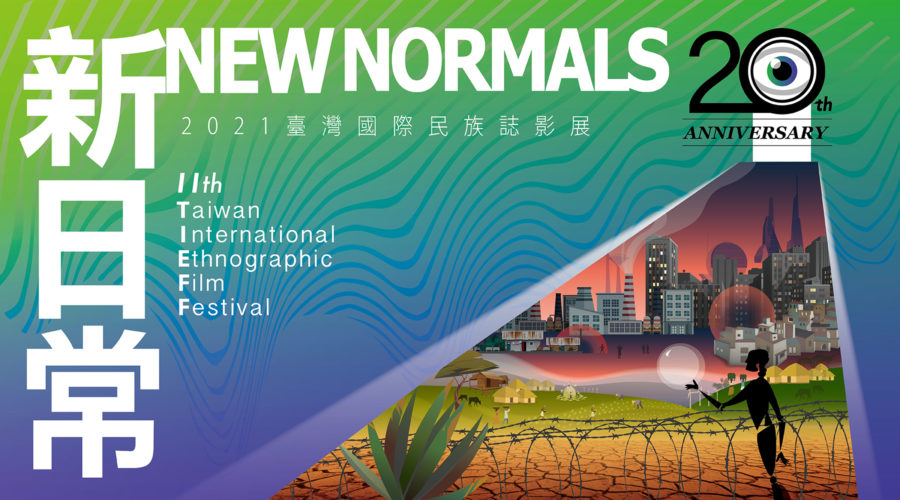孟加拉東南方的庫圖帕朗難民營(Kutupalong refugee camp)原本不是世界上最大的難民營。1991年,緬甸軍政府以「驅逐外國人」為由,展開「整潔與美麗國家行動(Operation Pyi Thaya,又譯Operation Clean and Beautiful Nation)」,迫使二十多萬羅興亞人逃離,其中許多人往西越過邊境,抵達孟加拉,定居在孟緬邊境的這個家。
然而三十年來,緬甸內部的族群衝突從未完全平息。2017年夏日,緬甸軍方以若開邦境內羅興亞叛亂分子武裝襲擊一處警察崗哨為由,展開清剿行動,後續一系列的衝突導致短短幾週內,就又有70多萬羅興亞人穿越緬甸與孟加拉接壤的土地,湧入考克斯巴紮爾地區(Cox’s Bazar district),使原本早已摩肩接踵的庫圖帕朗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難民營。在這個居所,不僅人們的日常隱私是一大奢侈,即使是基本的飲食、能源、學習也受到限制。
羅興亞難民危機躍上國際版面至今約莫四年多,然而細看衝突源頭,這片土地所面臨的考驗並非單純的宗教(伊斯蘭與佛教)、族群(羅興亞與緬族)、土地使用(先來或後到)、人權(受壓迫或自由)等紛爭,更其實牽涉了歷史脈絡下的身分認同等難題。難民的樣貌及夢想是相當多元的,然而在國際論述中極容易被扁平化、悲情化、去慾望化。逃難或移動的旅程中,往前是家、或往後是家,抑或此刻即是家?對於流動之人的描繪,如何跨越一言以蔽之的概述性表象、進而細膩關注個體的差異,往往是紀錄工作者及創作者最大的考驗。
《漂流:羅興亞故事(Wandering, a Rohingya Story)》只有不到一個月的拍攝期,導演梅蘭妮‧卡利(Mélanie Carrier)與奧利維爾‧希金斯(Olivier Higgins)面對如此重大的國際事件,選擇不以新聞紀錄片的視角、大量的資訊與數據呈現,而是以每個鏡位都如同一張向光源膜拜的平面攝影般的沉靜與肅穆,進行詩意的運鏡;音效時而切換於吟詩者卡蘭(Kalam,Kala Miya)的細語、時而切換至令人不安的混音、時而穿梭在難民營潮濕巷弄內的交談。與其說導演們在紀錄工作中忠實扮演了牆壁上的蒼蠅(fly on the wall),不如說他們選擇如同鬼魅般遊蕩、在忽明忽滅的空間裡觀看著眼前的一切。
幽靈一般的敘事,呼應了故事中人們在睡睡醒醒的夢魘間生活。猶如兩位導演過去的作品《八千公里的心靈之旅(Asiemut)》、《魁北克(Québékoisie)》皆以身體的移動推動影像紀錄的工事,《漂流:羅興亞故事》中也忠實捕捉了:羅興亞人穿越邊界的步伐、在爛泥堆裡踢足球的孩子們、爬上小丘唱歌的學生、進進出出家門抱怨丈夫與孩子們孱弱的婦女、排隊領取麵粉與米糧的居民、逃離緬甸後又回到家人身旁的翻譯者……生命如同一趟趟旅程,在移動的過程中進行實踐。只是何處為家?詩句、歌曲與幽靈並沒有給我們答案。
《漂流:羅興亞故事》同時在魁北克的國家美術館舉辦了一場展覽,將錄像裝置、平面攝影、兒童繪畫、立體實景模型、雕塑、詩詞、環境音等更多素材納入沉浸式的空間氛圍內,帶人們回到全世界最大的難民營。導演奧利維爾‧希金斯也在這次與我的信件與錄音訪談中,透露了從難民營回到家鄉後、被夥伴察覺的創傷。執筆此刻,羅興亞難民危機來到第四週年,縱然孟加拉政府以控制新冠疫情為由禁止遊行,庫圖帕朗難民營仍有數千名孩童趁此際進行抗爭,高喊「我們要正義」、「我們想要安全地回到家鄉」;然而,國際新聞大多已不再頻繁提及羅興亞人的命運,美軍撤離、塔利班執政的阿富汗佔據了所有國際版面。
在這樣的時刻,2021年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以「新日常」為名,播放距離我們三千多公里外的《漂流:羅興亞故事》。生活在《難民法》尚未誕生的臺灣,螢幕裡螢幕外的巨大鴻溝令人感慨,或許一段遙遠故事的映演,正提醒著我們,後疫情時代是一群人攜手度過難關、或各自明哲保身的分水嶺,莫忘這樣的時刻,總是考驗著地球每一份子共處的方式,縱然是微小的關注,也可能孕育出跨越地理與世代的火苗。
【與導演訪談細節,請見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