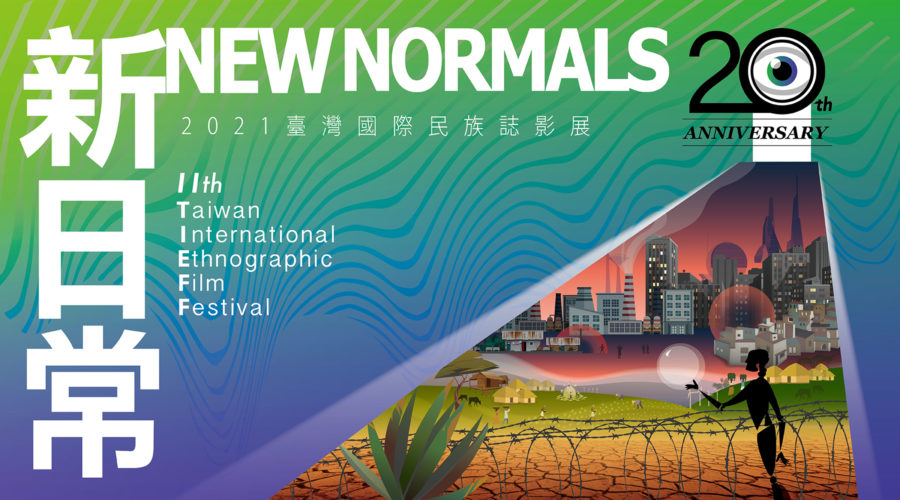【《漂流:羅興亞故事》推薦文章,請見上篇。】
2021年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越界新日常」系列中的《漂流:羅興亞故事(Wandering, a Rohingya Story)》,是一部詩意的難民營紀錄。有幸受邀推薦該作品,觀看過程中,認為與導演進行QA訪談或許能提供更忠實的詮釋。此次訪談以信件與錄音方式進行,受訪者為導演之一奧利維爾‧希金斯(Olivier Higgins)。為方便閱讀,回應內容已進行節錄。
Q:能和我們聊聊一切的起點嗎?拜訪庫圖帕朗難民營(Kutupalong refugee camp)的點子從何而來?
奧利維爾:2018年某一天,梅蘭妮‧卡利(Mélanie Carrier,此片共同導演)讀到何諾.菲利浦(Renaud Philippe,魁北克攝影師)的臉書文字,他當時正在庫圖帕朗難民營紀錄那兒的危機。將近15年來,何諾紀錄了不同的難民營,但在那篇文章中,他說自己從未見過如此嚴重的危機、疑問媒體為何不給予更多的報導?梅蘭妮感觸很深,提議我們不如約何諾見面、一起去做點事。於是何諾回魁北克後,我們見面了,也一起回到難民營。一開始,我們只打算去那裡走走,看能用相機做點什麼……或許是五分鐘、十分鐘的短片,但後來愈做愈大,成了現在這部長片,甚至邀請其他藝術家一起進行了跨領域的展覽合作。
Q:你們去過任何難民營嗎?你對庫圖帕朗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奧利維爾:我旅行時去過一些貧民窟,在我們的第一部紀錄片《八千公里的心靈之旅(Asiemut)》中,我們也騎單車經過了蒙古、尼泊爾等一些人們並不富裕的地方。但我從來沒去過難民營。抵達庫圖帕朗時,你首先可以感覺到他有多麼大、多麼擁擠,噪音從四面八方而來,它和其他地方都不同。或許因已經知道這裡的故事,你似乎能感到那背後有些悲劇、有些不正義,但那不是關於貧窮,而是你甚至無法想像的……人性的黑暗面與現實面。你同時也看到人們站在很長的隊伍裡等待食物。作為一個導演,攝影比我想像中還困難。因為你真的需要知道你為什麼需要拍這個、為什麼你在做某件事、你要怎麼做……我們一直在問自己。特別不容易的是,在如此現實的悲劇中,你一直走在道德邊緣,思考如何做出尊重他人的決定。
Q:為何取名為《漂流:羅興亞故事》?
奧利維爾:當我想像這部片該是什麼模樣時,我腦中有個畫面:人們並不存在,影像是模糊的,殘影、黑影提醒著這些人並不是任何國家的公民,不在官方文件中,沒有護照,不屬於緬甸,也不屬於孟加拉。人們有點像遊蕩、漫遊或漂流在難民營、無人區、三不管地帶,在每個日夜裡,在生命中,在難以預知的未來。作為外來者,我們試著以相機和人們互動。我們和口述者首菲(Mohammed Shofi)聊很多,他是片中卡蘭(Kalam,Kala Miya)的聲音。從2017年的危機以來,很多阿嬤為了逃離暴力,已經移動到孟加拉第三次了。所以我們決定,用遊蕩、漫遊或漂流(wandering)作為片名。
Q:片中的每個鏡位都像是一幅畫!這樣的攝影風格與你們之前的作品《八千公里的心靈之旅》及《魁北克(Québékoisie)》很不同,敘事的風格也有別於一般的新聞紀錄片,為何如此選擇?
奧利維爾:當梅蘭妮看到何諾的作品時,我們就打算做一部有別於新聞紀錄片的短片。在新聞資訊的日夜轟炸中,消息來了、又走了,有時我們很難感受到背後的人性。我們想將政治、歷史、經濟放一邊,多關注一些關於人及生命的故事。縱然是在悲劇裡,我們仍需要感到人們活著;影片關於廣泛人類的處境,但也關於特定的事件。視覺的部分,何諾的攝影風格和我們的想法很相近。我們打算在觀察的角度中,也搭配較為主觀的、藝術和詩意的視角。
Q:影片中有雙腿上下顛倒,嚇到了我。那一系列的影像及音效真特別,你可以多談談這個場景嗎?
奧利維爾:為了捕捉模糊的影像,我和何諾在現場各放置一台攝影機,有時我錄音、有時我錄影,他則有時拍照、有時錄影。我們隨興地在大家放鬆的狀態下移動。那時我們看到那雙腿,我到房間外面,從一根根竹子之間拍過去,像鬼一樣偷窺、看得不清不楚;何諾則捕捉了腿的上半部。我們把這些影像放在一起,就像鬼魂遊走,不知人類在做什麼。彷彿人生中總有些東西不太對勁。遊走在現實、非現實之間,人們肩上同樣扛著過去的鬼,被殺害的、不存在的、醒來卻以為還在的……那個難民營就像另一個世界。
Q:《八千公里的心靈之旅》、《魁北克》和《漂流:羅興亞故事》的拍攝過程似乎總牽涉著移動、在路上的狀態。對你們來說,移動或遷徙意味著什麼?
奧利維爾:哈,很有趣。對我們來說,移動是重要的。在《魁北克》片頭,一位人類學家說:「所有人類的故事都關於道路」。人們總是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在旅途中學習。作為紀錄片工作者,我們也在旅途中學習、進展、遇見人。在過程中,我們的觀點持續改變,不像劇情片你有個點子、然後就跟著它執行。你必須一直移動、一直產生新的想法、去感覺並形塑出你主觀的想法。移動身體有時是旅行,有時是冒險。我們在《八千公里的心靈之旅》和《魁北克》中騎腳踏車移動,我們在這部片中也在難民營裡漫遊,到處走,以成為在那裡漫遊的人。
Q:做為一個頻繁的旅者,我對於《八千公里的心靈之旅》和《魁北克》中所描述的那種「無法翻譯」及「縱然語言不同、也能用其他方式理解彼此」的時刻深深有感。但這次,在庫圖帕朗難民營的拍攝中,你有了一位fixer(翻譯員、導遊、喬事的人),這樣的拍攝過程,是否帶給你不同的感受?
奧利維爾:是的,那是不同的,甚至是很困難的。你知道,對於這樣的議題,你永遠都在走鋼索。其實《魁北克》的主題在這裡也很敏感,因為它碰觸了原住民和非原住民之間的關係。拍攝紀錄片是主觀的過程,很難真正客觀,只能接受一個事實,就是透過自己的觀點拍故事。我拍攝羅興亞人、和一位羅興亞人拍攝羅興亞人一定是不同的,我在這裡拍這座城市、和其他人拍這座城市絕對是不同的。我想我們試著給影片更多人性的角度,而非告訴大家什麼是事實。對,我想說的就是,在我們的片中,我們不想給予答案,而是試著挑起一些問題、或讓觀眾問自己一些問題。我們想跨越宗教或文化的定義,先從人的角度和感受出發,之後,我們才能更好地專注在難民營中的漂流、遊蕩,漫遊。卡蘭的觀點很重要,我們試著聆聽他、和他學習,也因此,我們請他寫一些和自由有關的詩句,也問他能不能寫和家庭、和愛有關的詩句?他寫了詩,我們問了他一些問題,他的回答也成為我們片中的元素。過程困難重重,因為翻譯很難精確,羅興亞語是一個口述語言,不是一個書寫的語言。舉例而言,卡蘭寫詩時,必須用英文寫,但我們必須翻譯成羅興亞語,因為影片中的口述是羅興亞語。另外,由於在難民營有太多的噪音,我們在片中無法使用卡蘭的原音,必須將整部《漂流:羅興亞故事》的口述都寫成英文,再請首菲錄音。首菲在來到魁北克前,曾經住在庫圖帕朗難民營18年,他沒辦法回到難民營聽卡蘭的聲音,只能透過英文稿理解。首菲必須即時翻譯片中所有的語言,比方他會讀一段口述的文字,然後想,那羅興亞語應該是這樣,但又好像有點長,於是換個角度去說、努力找真正的羅興亞語來說。整個口述對他來說充滿情緒,因為他有些家人還在難民營裡面,他有時會在這裡哭泣。我們打算不去外面的錄音室,而是在自家地下室即興弄個錄音室,也就是我現在和妳說話的這裡,因為在這裡可以舒服地坐著,慢慢地處理。有時會有些特別的時刻,他會很放鬆,找到好的時刻來回答這些錄音。
Q:在庫圖帕朗難民營的拍攝時間多長呢?
奧利維爾:不到一個月。
Q:我喜歡你們在這三部片裡都有些吟唱的元素。在庫圖帕朗難民營,你如何捕捉孩子唱歌的時刻?
奧利維爾:嗯,我非常喜歡在現場錄音樂,那和額外加入音樂有所不同。在《魁北克》中我讓歌手彈唱,讓現實引領著我,歌聲在跑,事件繼續發生,那是形而上的感受。在難民營有個組織提供兒童的安全空間(A Safe Space for Kids),有個工作人員告訴我這個小孩很喜歡唱歌、也很會唱,他常常在唱,要不要拍攝他?我想,好啊。我不知道歌詞和歌曲的含意,就跟著他拍攝。
Q:將《漂流:羅興亞故事》也辦成展覽的契機是?
奧利維爾:一開始想像的是短片,但難民營中的許多人都有故事要說,短片無法容納眾多的故事。在現場,何諾仍持續拍攝平面照片,那是他的熱情,他便提議我們除了紀錄片外,也同時進行其他形式的發表。當我們回來後,我們向國家美術館提議,他們表示興趣,我們也想或許可以做更大,也邀請了其他我們喜歡的藝術家一起,同時在機緣中認識了首菲,我們覺得在展覽最後聽聽他的故事很棒……計畫就愈滾愈大。這段旅程中,其他人的故事也感動著我們,這段旅程不能說結束就結束、立刻轉身、走向其他的事物。你必須尊重他們,於是就也努力找方法說這些故事。
Q:那麼在魁北克和國際的社群中,展覽和紀錄片的回饋如何?
奧利維爾:兩者的影響都很大。做這樣的紀錄片和展覽並不容易,因為帶著悲劇。我們試著把生活放在悲劇面前,譬如在泥巴裡玩鬧的孩子們,相對於父母輩的鬼魅,他們象徵了抵抗,他們值得那些光芒。很可惜,展覽只在魁北克舉辦,不過因為是國家美術館,所以很多人參觀,尤其展覽免費,這對我們來說很重要。通常看展必須付費,但我們請求展覽不收費,讓任何社經地位的人都能參與。《漂流:羅興亞故事》在公眾和藝術圈都獲得不錯的回饋。有個問題我們有時會被問到:相對於故事中的悲劇,畫面中的美麗令一些觀眾感到不舒服。不過對我來說,那種反差讓主題更強烈。當何諾和我在難民營時,有趣的是,走到哪裡都很美麗,因為走到哪裡都有自然光,而且地理環境與前景、後景總是相當立體。在營區裡,你常常可以看到太陽透過布幕投下光芒,這也是另一個我們必須面對的反差。也許我們並無刻意讓現場美麗,我們僅僅拍攝那裡的模樣;當我們選擇畫面時,也並不選擇僅僅美麗的畫面,而是專注於選擇有意義、說了某些故事的畫面。並非因為這是悲劇,畫面就必須醜陋、模糊、色彩黯淡啊,如果這樣,人們也可能不那麼在乎這個故事。
Q:《漂流:羅興亞故事》中的記憶與夢魘似乎並不易消去。那你們呢?作為影像工作者,你們是否有時必須承受情緒的壓力,尤其當你們所見的難民營生活,和你們自己的生活差距甚遠?
奧利維爾:當我回來時,梅蘭妮說我有點創傷的症狀。可能那是我不習慣的環境,何諾有更多的經驗,他的性格也比較能處理那個狀況。我沒有做惡夢,但我感覺有點不同。
Q:你如何處理這樣的情緒呢?
奧利維爾:當時間過去,我猜那種感覺漸漸消失了。做為一個影像工作者,你遇到的人、聽到的故事……我想人生中也是,只要你花時間聆聽人們的故事,你從他們身上學習,你據此打造你的故事,也打造了你自己。對我們來說,那也是旅程的一部分。《魁北克》的最後提到,當我們有了孩子,我們也得放手,讓他透過聆聽其他人的故事,去寫他自己的故事,那對我們來說很重要。在《魁北克》的開頭,我們引用了萊納斯.鮑林的「生命是分子之間的關係,而非任何一個分子的屬性。(Life is a relationship among molecules and not a property of any molecule.)」對我來說,聆聽其他人的故事,是我們做為人類連結與他人關係的過程,所以在旅程中,這種學習是重要的,某角度來說這並不容易,但它是重要的。因為你能學習的不只是政治、經濟的知識本身,而是人的故事。
Q:目前有什麼新計畫嗎?
奧利維爾:在計畫初期,我們不知道一部短片的構想會變成長片、又變成展覽。現在我們和首菲及這次負責展覽雕塑的視覺藝術家卡琳.吉布羅(Karine Giboulo)也展開了一部短片的計畫,將要述說首菲的故事。另外一個對我們重要的計畫是,既然我們有了兩個小孩,我們想談談從旅行者的身分轉變為父母的過程,本來打算在四個國家拍攝,但遇上疫情,乾脆在這裡拍攝就好。我們的小孩要上一年級了。這部影片會關於我們還是小孩時,都很純真、對世界的想法還很幼稚,只想玩;上學後,開始學習、閱讀,也從中認識世界,發現成人世界是什麼樣子。於此同時,成人總是──無論想不想──,灌輸著他們對世界的觀點給小孩。這是個有點哲學的片子吧,我們想藉此提問:我們給予小孩哪些自由,讓他們打造自己對世界的觀點?同時,我們也想對教育孩子的成人們拋出提問。